一夫一妻制是进步还是倒退?
责任编辑:psy898-念暖 发布于2022-08-28 17:37 浏览次
来源“心理氧吧”为原创,版权所有。本站有部分资源来自网络,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,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,请与我们联系进行处理。
相关人气资讯 :
-
 心理咨询师如何处理丧亲之痛?
心理咨询师如何处理丧亲之痛?
心理导读:希娜一直与母亲关系不好。在丧亲的这段时期,她母亲做出很大的努力来支持她,但是希娜发现很难接受这些帮助。与此同时,希娜的男友变得越来越情绪孤僻,最终他们... -
 乱伦行为的心理分析
乱伦行为的心理分析
心理导读:一些研究认为,父女之间乱伦中的父亲往往是文化水平低、有暴力倾向、社会生存能力低下者。他往往是用威迫、诱骗的手段和女儿发生和维持乱伦关系。女方往往是受害...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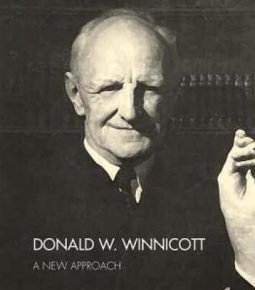 精神分析大师温尼考特
精神分析大师温尼考特
心理导读:心理治疗往往被视为太神秘、太不可谈了。温尼考特的个案写作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个案书,反而是更用心在每次的纪录,包括其中的过程和细节。对于不是心理治疗圈内的... -
 偏执型人格障碍有什么特征?
偏执型人格障碍有什么特征?
心理导读: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基本特征是对他人不信任和猜疑的普遍模式、以至于把他人的动机解释为恶意的。该模式起始不晚于成年早期、并出现于各种背景下。 ---www.psy898.c... -
 幼年丧亲对儿童身心发育有何影响(下)
幼年丧亲对儿童身心发育有何影响(下)
心理导读:200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,移民的健康状况变化与教育和居住时间有关,在某些情况下会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而恶化,因此移民史可能是这种差异的一种解释。未来对健康的... -
 抑郁症诊断测试量表
抑郁症诊断测试量表
心理导读: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把抑郁症称作心理问题的常规感冒。在美国,大多数进入精神病医院的患者都是因为抑郁症。即使你可能不懂重症抑郁症,但你很有可能经历过较轻... -
 《当哲学家遇上心理医生》人生答疑全集
《当哲学家遇上心理医生》人生答疑全集
心理导读:英国畅销书作家、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与英国著名心理治疗师安东尼娅麦卡洛,在《当哲学家遇上心理医生》中,为所有想要摆脱人生困境的读者,献上最精妙的哲学智慧... -
 如何记录自己的梦?
如何记录自己的梦?
心理导读:养成每天早上记忆记录梦境的固定习惯。这是熟能生巧的工作。但你得认清,做出完美无缺的梦记录是不可能的,因为做梦和记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。做梦若是演一出... -
 工作记忆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
工作记忆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
心理导读:当工作记忆超载时,早先进入的信息通常会丢失,这样可以为新的信息腾出空间。如果需要我们注意的信息挤满了工作记忆,那么我们也许不会注意到其他一些可能比较重...
-
心理咨询师如何处理丧亲之痛?
浏览440 次 -
乱伦行为的心理分析
浏览396 次 -
精神分析大师温尼考特
浏览286 次 -
偏执型人格障碍有什么特征?
浏览279 次 -
幼年丧亲对儿童身心发育有何影响(下)
浏览265 次
-
周雷专栏|心理咨询避坑指南 360 人浏览过
-
·自闭症诊断访谈量表(ADI-R) 226 人
·周雷专栏|心理咨询师能与来访者恋爱吗 267 人
·分裂型人格障碍会反复发作吗 225 人
·周雷专栏|孩子厌学怎么办? 352 人
·周雷专栏|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340 人
·周雷专栏|沙盘游戏治疗为什么这么火 201 人
-
心理咨询师如何处理丧亲之痛? 440 人浏览过
-
·精神分析大师温尼考特 286 人
·心理疾病诊断可靠吗 249 人
·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200 人
·阿希效应与从众的心理学研究 106 人
·抽动症能治好吗,治疗的方法有哪些? 222 人
·如何与来访者商定咨询目标 240 人


